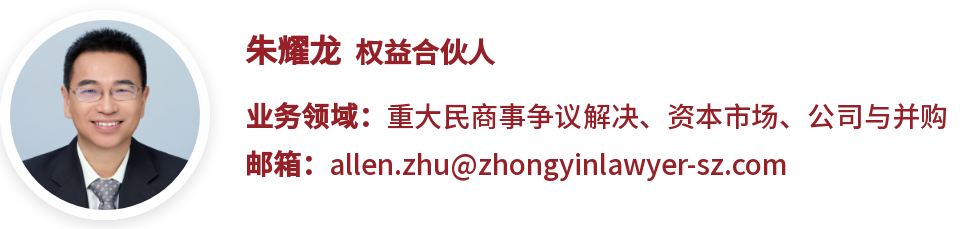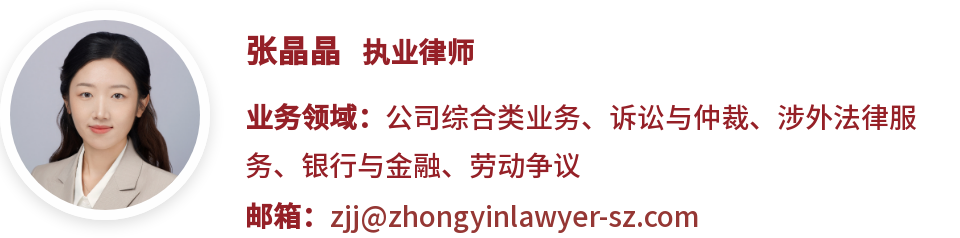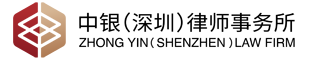北京中银(深圳)律师事务所谢兰军、朱耀龙律师团队律师代理的金融保证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,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(下称河南高院)于2025年7月10作出了(2025)豫民申XXX号民事裁定,指令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某境外公司与王某某(化名)金融保证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再审。该案历经一审、二审裁定驳回起诉,经申请再审,最终河南高院认定原裁定“适用法律错误”决定再审,折射出涉外民商事案件中“不方便管辖原则”适用标准的深层争议,为跨境金融证券类纠纷管辖规则的完善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。
一、案情脉络与争议焦点:跨境金融证券类债权的管辖之辩
本案核心法律关系为保证合同纠纷。再审申请人某境外公司因主债务人(BVI注册公司)证券保证金账户逾期未还款项,依据内地自然人王某某签署的《担保书》主张连带责任担保。王某某以“不方便管辖原则”提出管辖权异议,主张应由境外法院管辖;一审某市基层人民法院、二审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均以“境外法院审理更为方便”为由裁定驳回起诉。某境外公司不服,以“原裁定未严格满足法定适用条件”申请再审,河南高院审查后认定原审适用法律错误,指令再审。
争议焦点集中于:内地法院是否应适用“不方便管辖原则”驳回起诉?核心在于原审是否严格审查了“明显不便”“社会公共利益”等法定要件,以及法律查明、送达执行等实务操作是否构成审理障碍。
二、“不方便管辖原则”的法定要件与河南高院的裁判逻辑
(一)新民诉法框架下的适用要件重构
2023年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(以下简称“新民诉法”)第二百八十二条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“不方便管辖原则”,明确适用需同时满足五项要件:(1)案件争议的基本事实非发生于我国境内,法院审理及当事人参加诉讼均明显不便;(2)无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协议;(3)非专属管辖;(4)不涉及我国主权、安全或社会公共利益;(5)外国法院审理更为方便。相较于2022年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(以下简称“民诉法解释”)第五百三十条,新民诉法删除了“不涉及我国公民、法人利益”的绝对排除要件,将“社会公共利益”作为核心判断标准,并强调“明显不便”的实质审查。这一修订体现了立法对“过度礼让”的纠偏——不再仅因当事人国籍关联即排除适用,而是聚焦案件与我国的实际联系及审理便利性。
(二)河南高院的审查要点:从“形式符合”到“实质便利”
河南高院再审审查的关键,在于原审是否对“明显不便”“社会公共利益”等要件进行了实质审查。结合某境外公司再审申请中关于“不存在明显不便”的论证,法院重点分析了以下维度:
1. 诉讼便利性:送达、参与与执行的可操作性
王某某作为内地居民,其户籍地、财产均位于河南某市,内地法院向其送达诉讼文书无需跨境程序,相较于境外法院具有显著效率优势。某境外公司已委托内地律师代理诉讼,境内参与无实质障碍;而若由境外法院管辖,王某某需跨境应诉,时间、经济成本均显著增加。原审仅以“合同签订地在境外”为由认定“境外更方便”,忽略了当事人实际诉讼参与的便利性,属于形式化审查。
2. 法律查明与事实认定:障碍是否“重大”
案涉《担保书》约定适用境外法律,但某境外公司已委托境外律师完成法律查明并出具公证意见,相关证据(包括英文文本)亦经专业翻译及公证转递。司法实践中,外国法查明已非不可逾越的障碍——2020年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(一)》明确“外国法查明可通过当事人提供、司法协助等途径完成”,且本案法律查明已由当事人主动完成,中国内地法院审理不存在“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重大困难”。原审以“适用境外法律”作为排除管辖的理由,不符合新民诉法对“重大困难”的严格界定。
(三)裁判逻辑的实践延伸:明确跨境金融纠纷中“不方便管辖原则”的适用边界进而提供管辖指引
本案再审裁定的示范意义,在于明确了跨境金融纠纷中“不方便管辖原则”的适用边界:
其一,“明显不便”需以“当事人诉讼参与、事实查明、判决执行”等实际操作的客观困难为依据,而非仅以“法律关系涉外”或“准据法域外”等形式要件判断;
其二,“社会公共利益”需严格限定于国家主权、安全或重大公共秩序领域,避免将“个体公民利益”泛化为排除适用的理由;
其三,法律查明与证据公证的完成度应作为“是否存在重大困难”的关键考量——当事人主动完成相关程序的,不应再以“查明障碍”为由排除管辖。
三、司法实践的反思:从“过度礼让”到“审慎平衡”
(一)对“过度礼让”的纠偏:防止诉权实质剥夺
近年来,部分法院在涉外案件中存在“一异即移”的倾向,仅因被告提出管辖异议即裁定驳回起诉,忽视了对“明显不便”的实质审查。本案中,原审法院未全面评估内地法院在送达、执行等环节的优势,径行认定“境外更方便”,可能导致某境外公司面临“境外诉讼成本高、执行难”的双重困境,实质剥夺其通过内地司法维护权益的机会。河南高院的再审裁定重申,“不方便管辖原则”的初衷是避免司法资源浪费,而非削弱当事人诉权;法院需在“国际礼让”与“权利保护”间审慎平衡,对“明显不便”的认定应采取“严格标准”。
(二)跨境金融纠纷的特殊性:管辖规则的适配性
随着内地与境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深化,“境外债权人-内地担保人-境外主债务人”的三角债权结构日益普遍。此类纠纷中,担保人财产多在中国内地,判决执行的便利性是当事人选择管辖的核心考量。本案中,王某某的可执行财产均位于中国内地,中国内地法院审理更有利于判决落地;若移送境外管辖,某境外公司需通过区际司法协助程序申请执行,周期长、成本高,与“便利诉讼”原则相悖。河南高院的裁判逻辑回应了这一现实需求,强调跨境金融纠纷中“执行便利性”应作为“明显不便”审查的重要因素,为同类案件提供了可预期的管辖指引。
(三)法律适用的统一性:新民诉法与司法解释的衔接
新民诉法实施后,部分法院仍参照旧司法解释(如民诉法解释第五百三十条)中“不涉及公民利益”的要件,导致法律适用不统一。本案再审裁定明确,新民诉法作为上位法,其“社会公共利益”要件已替代旧解释中的“公民利益”要件,司法实践应优先适用新民诉法的规定。这一立场有助于统一裁判标准,避免因法律适用冲突引发的管辖争议。
四、结语
总结:改进涉外金融纠纷管辖的解决方案,提升中国内地作为跨境金融纠纷解决地的吸引力。
某境外公司与王某某案的再审,是对“不方便管辖原则”适用标准的一次精准纠偏。它揭示了新民诉法框架下,涉外案件管辖应从“形式关联”转向“实质便利”,从“过度礼让”转向“审慎平衡”。对于跨境金融纠纷,中国内地法院应立足“执行便利性”“诉讼参与成本”“法律查明完成度”等实际因素,严格审查“明显不便”要件,避免因程序性认定错误实质剥夺当事人诉权。这一裁判逻辑不仅维护了司法公正,更通过明确的规则指引,提升了中国内地作为跨境金融纠纷解决地的吸引力,为涉外法治建设注入了实践活力。
律师介绍